“周五下班飛中國”,最近韓國人掀起了一股到上海過周末的新潮流。從淄博趕烤,到天水麻辣燙,再到如今備受韓國人喜愛的麻辣龍蝦、燒烤、海底撈等,“美食+文旅”魅力十足。數字時代,美食為什么成了人與世界、人與人之間連接的重要載體?在那些備受讀者好評的“舌尖上的圖書”中,我們或許能找到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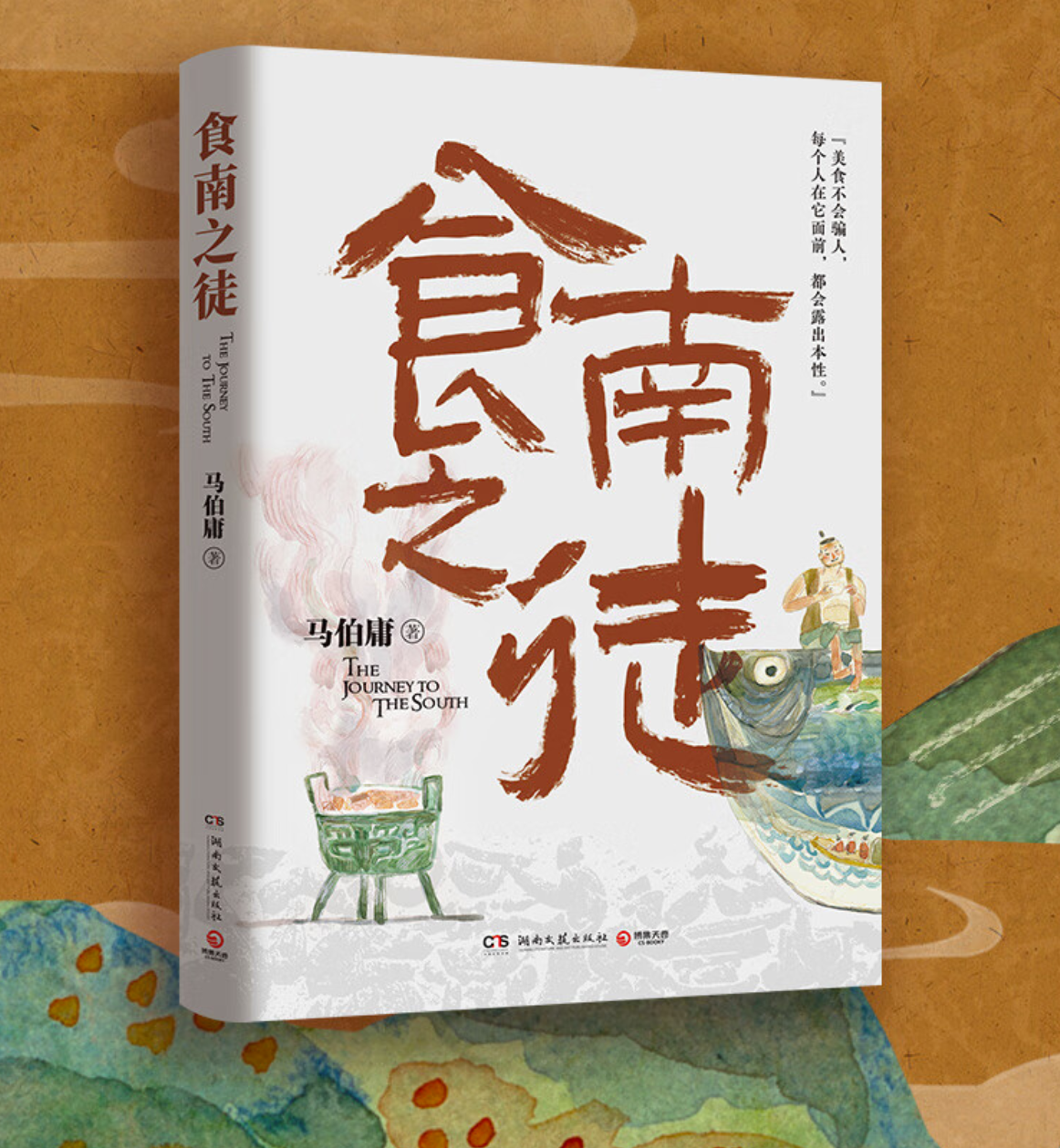
美食并不“小”。馬伯庸的長篇歷史小說《食南之徒》,近日入選豆瓣2024年度小說榜單。書中,他通過漢使唐蒙的味蕾奇遇,見微知著地打開了西漢時期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乃至版圖開拓史。烏橄欖,生津清甜;仙草膏,可解熱暑;雜燉,異香撲鼻……唐蒙口若懸河地講美食,其中“枸醬”這一小小的食材,竟然成為一個國家滅亡的關鍵性角色,也讓讀者感慨“吃貨的力量有多大”。唐蒙和“枸醬”的故事在《史記》中確有記載,唐蒙初到南越國(今廣東、廣西等地),吃到了一種名叫“枸醬”的美食,他發現這種醬產自蜀地,經夜郎國(今貴州)來到南越國。唐蒙于是建議漢武帝出奇兵,取道夜郎制服南越,從而重塑了西漢版圖。一向善于“在歷史的縫隙中”開拓的馬伯庸,開啟了以美食解鎖歷史的文化之旅。
“天下至真者,莫過于食物。好吃就是好吃,難吃就是難吃,從來不會騙你。”馬伯庸在廣州南越王博物院參觀時,因為深究文物細節有了新發現——“趙佗遠在他鄉仍不忘攜帶故鄉的棗樹”,這不僅成為《食南之徒》的創作起點,也凸顯出美食作為一種跨越地域的情感紐帶,如何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連接故土與新居、過去與現在的關鍵角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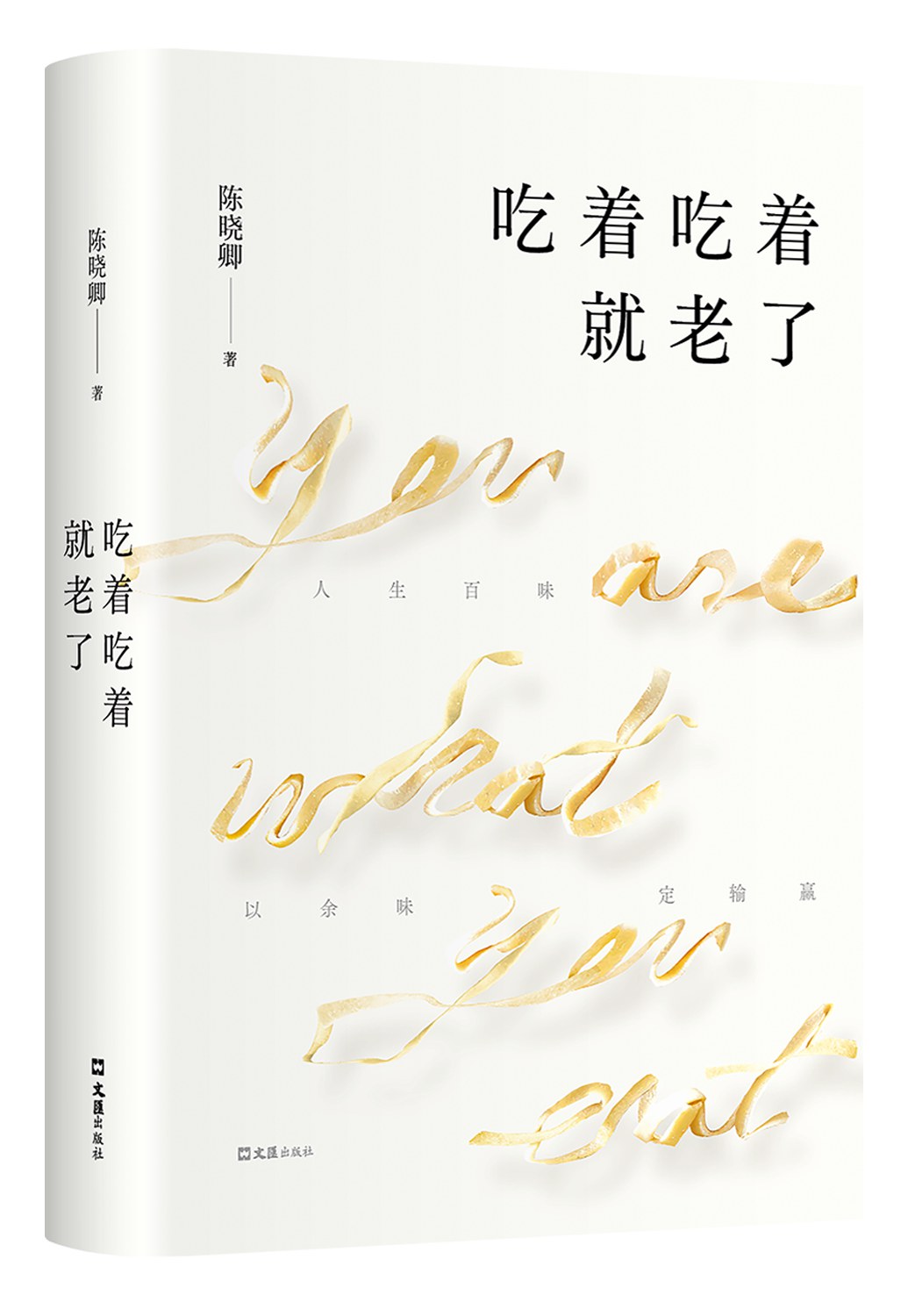
“我們曾經的飲食習慣、偏好,甚至經歷過的時代,無一例外地遺落在我們飲食的DNA里。它標識著你的歸屬,這種歸屬感牢不可破。”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制片人陳曉卿在最新散文集《吃著吃著就老了》中這樣感慨道。
從17歲出門遠行、進京求學講起,到成為美食紀錄片導演,陳曉卿以自己經歷為經線,以對食物的認識和態度為緯線,編織出一個關于美食和人生的故事——兒時,六毛錢的缸貼子、鄰居家的西瓜醬、第一次下館子時燙嘴的蕭縣羊肉湯,這些味道刻在基因里,成為鄉愁的載體;在北京,作為外地務工人員,府右街的延吉冷面、寒夜里24小時的馬華牛肉面、與朋友一起吃肉串喝工業啤酒聊哲學的時光,食物承載著他的生活點滴與情感。就像書名呈現的那樣,書里有食物的“香氣”,更有人生的“況味”。“吃家常菜得到的滿足感,吃燕鮑翅并不一定能得到”“我眼中的美食,不僅僅是認識世界最有趣的通道,也是人與人交流最便捷的途徑”“一座城市,最吸引我的,從來不是歷史名勝或者商業中心,而是菜市場。只有在菜市場,還能從一些地域性的物產上,分辨出城市不同的風貌”……這些陳曉卿從美食上生發出的意義,或許也是當下“美食+文旅”成為重要載體的原因:美食里,有故鄉,有人情,有生活的多樣性。就像陳曉卿書中寫到的那樣,稻米通過不同的加工手段,居然能演變出那么多美食,粉、圓、粽、糕、糍、丸、糟、糜、堆……即便是和粑粑性質類似的年糕,也有不同的稱呼。僅在廣東一地,客家人稱之為粄,潮汕人稱之為粿,而粵西人則叫它籺,這一切,是多么有趣的現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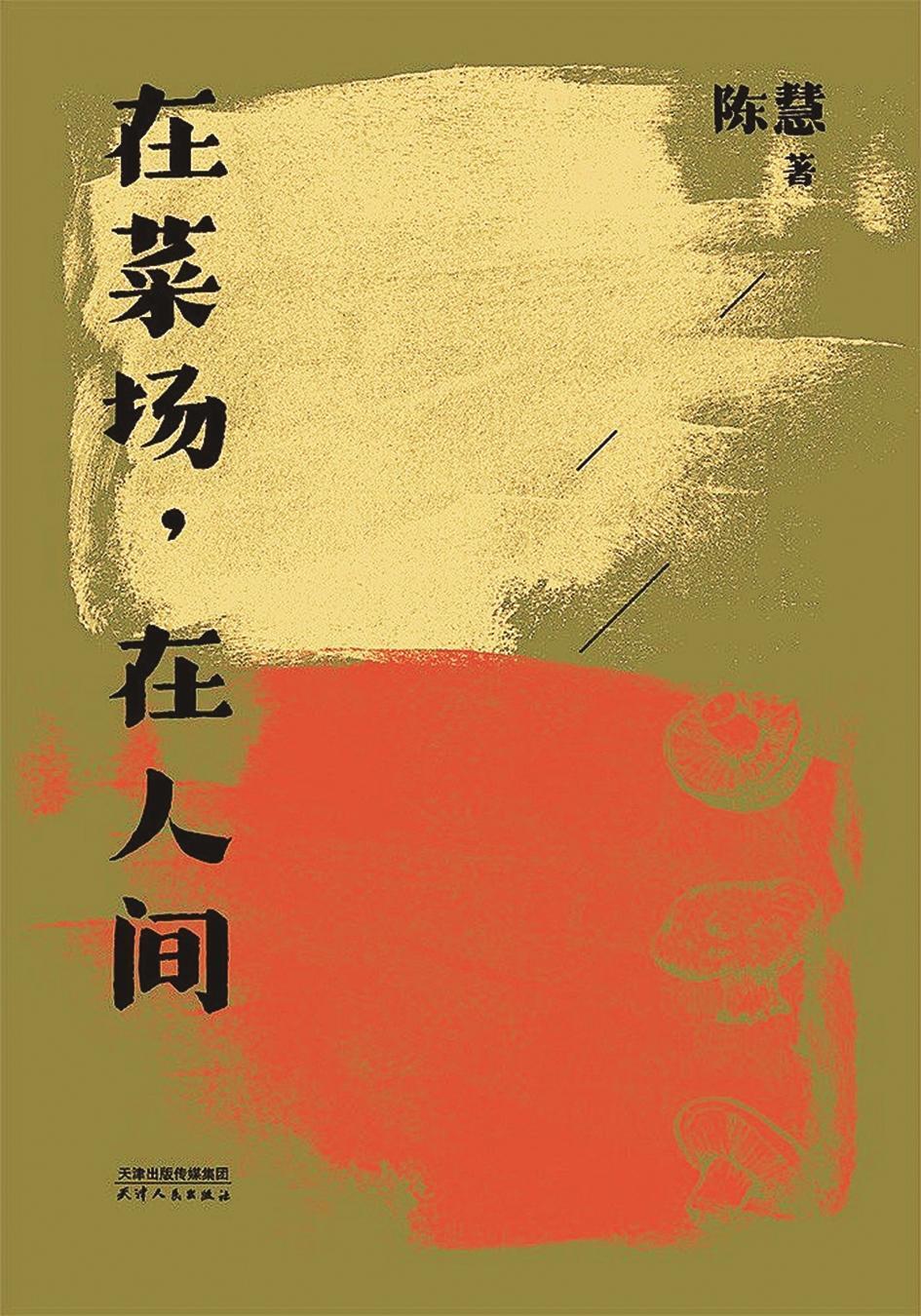
溫情脈脈的美食背后,還有熱辣滾燙的人生。作為素人寫作的佼佼者,在菜場擺攤18年的“菜場作家”陳慧則用一本紀實散文《在菜場在人間》,打開了另一個視角的“菜市場觀察日記”。菜販、肉販、包子鋪、餛飩店、賣山貨的、攤燒餅的、修鍋的……這些習以為常的身影構成了菜市場的日常群像。而陳慧以細膩質樸的筆觸,穿透平凡表象,將那些被忽略的攤主故事娓娓道來:佟良貴堅守承諾,為離世友人托起孩子的未來;阿瓜雖身有不便,卻以赤子之心反哺父母養育之恩。這些平凡人在生活窄縫中綻放的光芒,正是人間煙火的真諦所在。當合上書本,再度踏入菜場,或許那熟悉的喧囂聲中,每一張面孔都將被賦予新的溫度,生長出“附近的力量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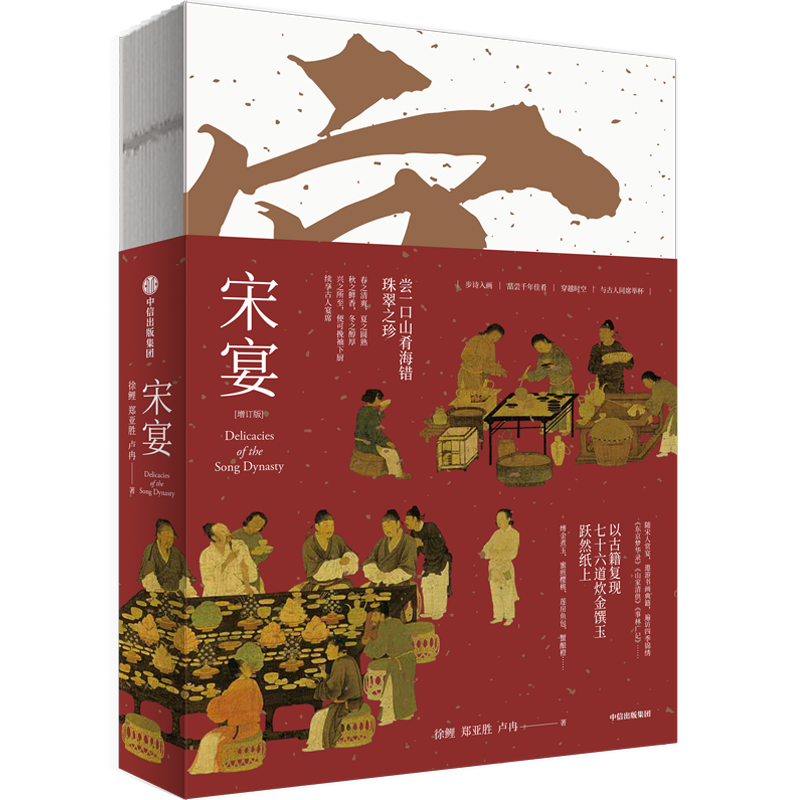
當然,這些書中也真的有很多跟“吃”本身有關的細節。比如陳慧在書中提及了如何區分真假番薯、辨別土雞蛋、散養豬的知識;陳曉卿也分享了自己找好吃小飯館的秘訣,根據他的經驗,好吃的飯館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,那就是招牌上基本包含了廚師或老板的名字,因為這是他們對自己手藝的一種自信。而三位青年作者連續推出的古人餐桌系列圖書《宋宴》《元宴》則真的是食譜。以《宋宴》為例,作者根據《山家清供》《中饋錄》等宋元典籍文獻記載,以一種創新的方法,“復刻”了76道宋朝美食,按時令編排,囊括宮廷菜、文人菜與平民菜三級,涉及熱葷、素菜、冷盤、羹湯、粥面、糕餅、飲料、果子八類,不僅有具體做法,還自帶文化基因。比如“煮魚”是北宋文士蘇軾的拿手菜,他在被貶黃州的那段人生低谷期,時常自己煮魚來吃。這些書籍不僅讓我們領略到美食的魅力,更讓我們感受到文化與生活的交融之美。
作家馬伯庸曾經說過,美食是中國人最大的公約數。穿梭于“舌尖上的閱讀”中,我們不難發現,美食不僅是滿足味蕾的享受,也是洞察世界的一種方法。當我們為生活中的這些小事雀躍時,鮮活的生命力便也自然綻放。
